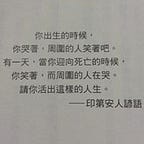2013年底,在結束了英國內觀長課程完後,我回到倫敦,搭乘歐洲之星穿越了海峽來到的法國巴黎,準備要到法國的內觀中心待一陣子。
法國的內觀中心在巴黎的近郊,離巴黎車程大約一個多小時的距離。該中心的歷史非常悠久,是歐洲最老的內觀中心之一。本以為會是一個房屋老舊看得出歷史痕跡的中心,卻發現該中心的建築和設施卻是格外的新穎,我想可能是近幾年重新翻修整頓過的吧。
與英國內觀中心的宏偉壯闊比起來,法國內觀中心顯得特別的嬌小。從辦公室的入口出穿越過去,只看見幾棟建築物以大禪堂為中心點,成放射線狀座落於它的四周。
由於我在法國的期間內觀中心沒有課程,所以我報名了十天的園區維護。全世界的內觀中心都差不多,每年都有兩次的園區維護,一次在春季,另一次在秋季,在這段期間中,來中心服務的法工可以好好將中心打理整頓一翻,做一些平時在課程期間無法做的工作。
來參加園區服務的法工大約有十位左右,大多是來自法國當地的舊生,除了幾位資深的法工之外,還來了幾位正在休假的大學生。我被安排住進一間獨立的套房,該套房中與其他國外的中心一樣,所有的設備是應有盡有,非常的舒適。但其特別的地方在於裡頭沒有任何的隔間,只有一整棟原木建造而成的房間。雖然淋浴室有隔著玻璃,但馬桶就座落在房間裡面的一個角落,與床鋪之間只有隔著一個矮牆,一打開窗門所看見的是一整片的樹林,有一種非常隨性且豪邁的原始感。
艱辛的園區服務
每一天晚上用完晚餐後我們都會在餐廳集合,中心經理會把隔天要做的工作陳列出來,大家可以分組來進行不同的工作。男生大多是從事戶外需要勞力的工作,而女生則從一些室內清潔的工作。
頭幾天我與其他三位法工負責挖掘一個地道,我們的任務是挖掘一條深約一公尺、長約二十公尺的地道,從男生宿舍連接至另外一棟新建好的宿舍,此地道的用途是用來埋藏電子鐘的線路。
首先,我們要先把草皮像切蛋糕一般切割成一塊一塊的,挖起來先擺在一旁,然後就是拿鏟子不斷地將土挖上來。我們從早上七點半吃過早餐後,一直挖到早上十一點。用完午餐稍作休息後,再一路馬不停蹄地挖到五點鐘。日復一日地挖掘這條通道,真是費了許多力氣。帶領我們的是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法國人,他留著一頭放蕩不羈的長髮,臉上滿佈紋路的他,看起來像是個街友。
『他年輕時候應該沒有好好地照顧自己』我這麼想著。
充滿陽光和幹勁、有著源源不絕能量的他是我們的領頭羊,每當我們挖到堅硬的大石頭無法再往前一步的時候,他總是毫不猶豫地跳下鴻溝,用盡各種工具和方法將石頭弄鬆,再和我們一起將石頭取出。 有著他堅實可靠的肩膀,讓我們就算挖到筋疲力盡時,也覺得我們可以完成此任務。
在與他一同揮汗工作的時候,我從他身上聞到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。我一邊努力地挖土,一邊再想到底在哪裡聞過這樣的氣味。看著他消瘦的背影,聞著他身上散發出的體味,我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個印度人的影像。我揉了揉眼間再仔細一看,眼前的這位老兄明明是位法國人,為何我會有這種錯覺?
吃飯時間與他聊了起來,才終於解開了我的疑竇。原來他真的是半個印度人!不是說他有印度人的血統,而是他在印度待過十多年的時光。
『我年輕時是個放蕩的嬉皮,和許多來自歐美國家的年輕人一樣,在印度四處遊蕩,過著離經叛道的生活。那年,我在德里機場被逮到時,身上被搜出許多大麻和毒品,然後我就被關進德里的提哈監獄。』他告訴我。
我聽到這裡不由得瞪大眼珠子,不得不打斷他:『慢著,你說的是那個『提哈』監獄嗎?』
有上過內觀課程的人都知道,在課程結束後我們會欣賞一部名為『牢關』影片,影片紀錄著內觀禪修在印度監獄中發展的歷史。影片中描述提哈監獄是印度規模最大也最混亂腐敗的監獄,該監獄最著名的就是關了許多重刑犯,他們所犯的罪行聽起來真的令人髮指,而裡面環境也真的宛如人間煉獄。影片中也有訪問到幾位西方人,他們在印度犯法而被囚禁這個惡名昭彰的監獄。
他眼角往上一揚,眼神彷彿回到了當時的場景:『沒錯,就是牢關影片中的那個監獄,我在那裡待了十幾年。開始的前幾年,我真的感覺生不如死,覺得這輩子就這樣完了。當內觀被引進到提哈監獄的時候,我就是頭幾批的學員,我一接觸到內觀就讓我徹底改變了,我也開始重新思考我的人生。而後的幾年,我都在監獄裡面當內觀法工,服務其他受刑人。現在想想,我還蠻感激上天給我的懲罰,如果不是這樣,或許我就不會接觸到內觀,現在也不會站在你面前,哈哈。』
他娓娓道來不堪的往事,感覺沒有一點難過和悲傷的情緒,反而像是在說著其他人的故事和遭遇一般。每個人接觸內觀的機緣都不盡相同,有的人尋訪了許久終於得遇,有的人卻無意間因為某個機緣而碰上,而這位法國老兄的機遇之奇堪比佛典裡面的故事,他從一個無惡不做的人,轉變成一位積極行善的人,聽到這樣的事蹟不僅讓人對這個方法產生極大的信心,也對佛陀以來一直將這方法延續下來的所有祖師們感到無比的感激。
這也讓我想起來葛印卡老師常說的,其實我們跟關在監牢裡面的人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,我們都是我們內心煩惱和習性反應的囚犯,我們不斷製造不善的業行讓自己受苦,其實我們不是真正的自由。而內觀幫助我們面對內心的煩惱並改變心裡深處的習性反應,我們開始學習掌控自己的內心,不隨著自己的慣性起舞,而成為自己心的主人。眼前的這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,不是嗎?
他說道:『從監獄放出來之後,我回到了法國過著清靜的生活。我現在很少參加十日課程了,我在郊區的森林中有一座小屋,現在我都在那裡自己閉關十天,那才是真正的寧靜呢。』
更為艱鉅的挑戰
隨著挖掘地道的工作告一個段落,第四天開始我被安排到另外一組,他們的工作因為人力的不足而導致進度落後。我隨著其他三位法工來到倉庫,拿了雨靴和手套,把一些工具丟到貨車上,就和他們跳上貨車前往工地了。
這次是進中心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坐車繞了中心的園區一周,該中心佔地真的是大到難以想像,不僅擁有一整片森林和菜園,從門口到餐廳開車也要好幾分鐘。我們出了中心大門,來到一處空曠的區域,只見有好幾座像是游泳池的蓄水池,有的水深、有的水淺,原來這裡是該中心的廢水處理廠,也是囤積雨水的地方。
我和他們繞過一座座龐大的蓄水池,來到一處蠻荒的空地。該空地大約有兩座籃球場的空間,裡頭滿佈樹根和泥濘,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所有的樹根連根拔起,將這塊地整治起來當蓄水池。我看著那無數盤亙錯綜的樹根與滿佈的泥濘,不由得頭皮發麻,這聽起來根本不像我能勝任的工作。只見他們穿好了雨靴戴起了手套,拿起大鋤頭和鏟子就跳到泥地去工作,我也只好跟著他們一起赴湯蹈火了。
我拿起了大鋤頭,朝著離我身邊最近的樹根用力地砸下去,只見樹根一動也不動,手卻一陣陣發麻,連試了幾次都無法撼動它。不斷地嘗試之後,我逐漸抓到訣竅,首先要拿起耙子把樹根周圍的泥濘挖掉,然後拿著大剪刀把樹根相連的枝幹一根一根切斷,最後才拿起鋤頭朝著樹根砍下去,將它整個連根拔除。我們有時候自己一個人把周遭的樹根挖除,有時候兩三個人一起對付一根龐大的樹根。
有些樹根看起來很淺,但當我想要一口氣把整個樹根批成兩半時,才感覺到他的根是如此深埋地底;有些樹枝看起來很難對付,卻是兩三下就挖起來了。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,我也逐漸熟練各種工具,以及如何對付各式各樣的樹根了。
突然間我好像悟到了什麼,其實挖掘樹根和我們在禪修中根除我們的煩惱的染污是相似的。我們不斷地透過覺察身心感受和對它們保持絕對的平等心,感覺所有的感受一一升起滅去,藉以將我們心中根深蒂固的業行拔除。有時候粗重的感受可以很容易地被消融,有時候卻是根深蒂固,固執地不想要被挖起來。這時候我們就必須先將注意力從該感受的核心中移開,開始遍掃全身,去感受核心所牽連到的地方,我們必須有系統地先遍掃身上較細微的感受,然後再回到核心,直到全身上下所有的感受都一一消融,連感受的核心也一並消失。
如同在挖掘樹根時我們必須選擇使用各種工具一樣,我們在禪修時每一刻所面對的心理和生理的情況都不相同,我們必須很善巧地審視當下所面臨的每一種情況,再選擇正確的方法來對峙每一個處境。
就這樣在泥地工作了三天,看到被我們挖起來丟在一旁的樹根已不計其數,登時有種成就感。然而每當我們望向尚未處理的空地,才知道我們處理的只是一小部分。啊,這真是個既苦悶又艱辛的工作,要根除所有的樹根真的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。這種感覺好像每次靜坐時,當看見到內心的染污逐步被根除的舒暢感,正要沾沾自喜的時候,才會覺察到在更深層的地方還有更多的染污,我們的工作還沒完成,只能更有耐心地繼續禪修下去。
到了第七天,組長看了一下我們的進度覺得很滿意,雖然這次的園區服務是無法將所有的樹根全部清除乾淨,但也算是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,才結束了此工作。
困難度持續升級
第八天的早上,我與一位來這裡長期服務的義大利人攀談。留著帕華洛帝的大鬍子,有著一個小肚子的他,一看就知道是義大利人。他名字叫做尼可羅(Nicolo),來自北義,平時都在義大利內觀中心的他,這次找到機會來到法國來做法工。由於北義大利在地理位置緊臨其他歐洲國家,所以他和許多我遇見的北義人一樣,會說多種語言。除了義大利文之外,他還會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和一點點德文。住過義大利的我以簡單的幾句義大利文與他攀談,也聊起我在義大利內觀中心的經歷和在該中心認識的人,果然讓他感到很親切,有點他鄉遇故知的感覺。
早餐過後,有一位有著虎背熊腰的法國人來帶我們到中心的倉庫,看來又有新的任務要執行了。只見倉庫外頭有無數被砍下來的巨大樹木,堆成一座小山丘。透過尼可羅的翻譯,我才知道我們的任務是要將這所有的樹幹,搬到倉庫內堆疊起來。我的老天啊,這些樹幹每根都有三四公尺長,最粗的有我的腰圍一般粗,最細的也有我的大腿一般粗,我們竟然要徒手將它們搬來搬去?只見我們的領隊已經開始搬了,我和尼可羅對看了一眼,也只好開始嘗試去搬動他們。
我們只能盡可能挑選最細的樹幹開始搬,先把樹幹放到自己的腰際邊,然後再一步一步慢慢地將它們拖到倉庫內。有些樹幹實在太重,我們只好兩個人一人搬一頭。我們的領隊是個忠厚老實的莊稼漢,平時就在伐木種田的他,手臂胳膊比我的大腿還要粗,這種粗活對他來說真的是駕輕就熟。他雙手各環抱著一根樹幹,很寫意地扛起擱在肩頭上,散步到倉庫後再輕輕地把它們放下。反觀我和尼可羅則費勁了吃奶的力氣才能將樹幹拿起,再花九牛二虎之力搬到倉庫,然後就是碰一聲,重重地將他們摔在木頭堆上。
有時候領隊看我們走的搖搖晃晃時,還會伸出他像芭蕉串的大手幫我們扶一把。我們真的對他的天縱神力感到佩服,也感謝他這麼照顧我們,雖然他的外表是粗獷的,但我感受到他的心地是如此的柔軟,如此的善良。
結束了十天的園區維護之後,我彷彿經歷了一場艱難且深刻的戰役。現在回想起來,或許這些艱苦的工作,正是我的課題。在職場上,我在自己職務的範圍和專業的領域中有著一定的把握和自信,總覺得自己像是超人般無所不能,直覺得任何棘手複雜的事情到手來都能迎刃而解。
然而透過這些粗重的工作,我才知道自己的一點小聰明在許多地方都是微不足道,派不上用場的。這也讓我覺習到謙卑,這的世界上有太多事情不是那麼理所當然,若不是有這麼多的人日以繼夜地辛勤地工作,我們怎麼會有完善的設施和環境,讓我們可以毫無阻礙地完成我們的工作?若不是有這麼多隱姓埋名的人默默地在服務著我們,我們怎能安然地度過每一天?一切都是得來不易,我們應該無時無刻地保持一顆感激的心,並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。
在勞力服務期間,能慰勞我們辛苦的就是每天法工阿姨細心為我們準備的料理。該中心的餐點料理真的是美味可口至極,每一套菜色好像都是從高檔餐廳端出來的一樣,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我很訝異法國的素食料理竟然是那麼的精緻,有別於其他歐洲中心的清淡和簡單。從當地的法國法工口中得知,原來這些料理都不是傳統法國菜,因為法國人是不吃素的,這些其實都是法工媽媽們自己的創意,利用當季的食材和法國家常菜的處理方法,充滿慈愛細心烹調出來的。而讓我們每個人都允指難忘的一道菜就是野菇。和著奶油用小火燉煮,遠遠就能夠聞到其香氣,真的是讓人食指大動。但這種『米其林』等級的美味不是每天都有的,只有當一位住在中心附近的法工Djahan出現,我們才有機緣享用到這美食。
在這世界上總會有一些人,當他們出現時,周遭的人都會感到非常的快樂,喜歡圍繞在他們身邊,和他們說說話;每他們不在時,大家都會非常想念他們。而Djahan就是這樣的人,雖然他的行動有點遲緩,說話也有點結巴,但大家非常喜歡他,每個人看到他時臉上都會洋溢著笑容。他出現時總是會帶著一個竹子編的籃子,後來得知原來中心的野菇都是他特別去為我們採集的。我對他感到十分的好奇,請他一定要找機會帶我一同去採野菇。在中心的最後一天,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,Djahan沒忘記他對我的承諾,在餐廳靜待我工作結束,特地幫我準備了一個籃子,要帶我到森林裡去採野菇。
我們走出餐廳,穿越了草原,進入了森林區。興致沖沖的我,立即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出那些野菇。起初找到的都是大大的、顏色鮮豔的香菇,當我要採集時就會被Djahan阻止。
『那些都是有毒的香菇。』他溫柔地提醒著我。
只見他在森林間緩步著行走,感覺很漫不經心,卻是精準至極。他憑著自己的經驗和靈感,很輕鬆地就在樹木底下或是樹叢間找到那些不起眼的黑色的野菇。我也有樣學樣,在幽暗的森林中尋找著很輕易就能錯過的人間美味。
課程結束後,我與兩位法工應Dhajan的邀請來到他中心旁的家。原來Dhajan是名藝術工作者,他有著很特別的藝術天份。他靈感來自大自然,取材也來自大自然,經常受邀到處去展覽他的藝術作品。他個子不高,但他的一雙手卻異常的大,和他握手的時候我就感到那雙大手充沛的生命力,我想那是他與生俱來最好的禮物,任何不起眼的事物經過他的手,就變得充滿生命力的藝術品。中心裡張張以樹枝編織而成的椅子、形狀大小不一的木頭所組合而成大衛之星、牆壁上寥寥數筆佛陀禪坐意象圖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結束了法國的十日園區服務之行,我與在服務期間認識的朋友們一一道別,感謝他們這陣子的照顧,並展開我下一段的旅程,我預計到南法待一段時間,帶我的母親一同去旅遊後,再前往瑞士的內觀中心(延續閱讀:有著印度靈魂的瑞士修行者Thierry)。而緣分真的很不可思議,幾年後,我在印度偶然遇見在這裡認識的尼可羅,我們倆竟同一天來到菩提迦耶,一同在菩提樹下靜修十幾天,之後不約而同在同一天離開那裡,那又是另外一段神奇的經驗了。